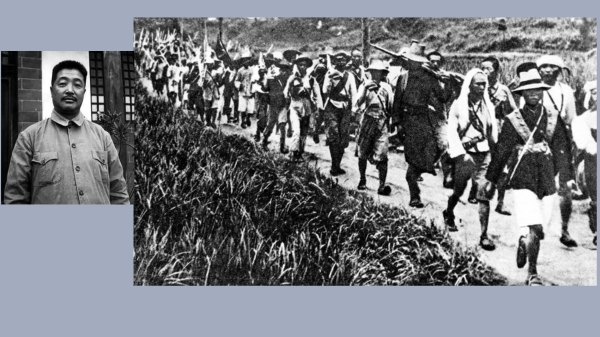
贺龙和被围剿的红军。(图片来源: 网络图片)
在中共官方宣传中,红军在“长征”中“食不果腹,被迫吃草根、啃树皮、吃皮带充饥”
红军长征被描述得极其艰苦,饮食方面的困难尤为突出,参加长征的红军每天冒着枪林弹雨,食不果腹,被迫吃草根、啃树皮、吃皮带充饥?这种描述符合历史事实吗?为什么在亲身参与“长征”者的回忆中,出现了丰盛的饮食实例?
一、中共内部人士回忆:红军吃麻辣鸡丝加大白米饭
有中共内部人士证实,实际上长征途中伙食相当好,每天每顿都是大米饭。
李一氓,生于1903年,1925年加入共产党,中国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科长,南昌起义参谋团秘书长,参加过红军所谓的“长征”,后任陕甘宁省委宣传部长,新四军秘书长。之后,李一氓还曾先后任苏北区党委书记,华中分局宣传部长,大连大学校长等职。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中共驻缅甸大使,国务院外事办副主任,中联部副部长,中纪委副书记等职。1990年12月,在北京逝世,终年87岁。
《李一氓回忆录》中这样叙述:1934年冬,我到闽赣区前线视察工作,当时正是放弃太宁、退守建宁的时候。我得了副伤寒,我的同乡前方卫生部长彭真是我的主治医生。治好病后,当时的前线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发了我十个银元的休养费。临行前,李克农让我感谢彭部长,实际上是让我做一顿饭请他们。当时大概一桌有八九个人,在建宁这个闽赣边的小城,有鸡和肉。用江西、福建的一种名叫地瓜的一种块根,切成片配在猪肉片里炒了一盘“滑肉”。又用建宁的建莲剁成泥,做成莲子泥,又甜又烫。另外还有麻辣鸡丝、麻婆豆腐之类,他们吃后都很满意。
我还想前方每天都是大米饭,这次该吃顿“臊子”面。我就擀了鸡蛋面,并到街上买来几大碗豆腐脑,做成“臊子”豆腐脑汤面,大家都觉得新鲜,爱吃。
1934年秋天,开始了长征。在长征路上,有时供给好,有时供给不好,这主要看地区了。湖南、四川都不错,广西、贵州、云南差一点,当然更差的是川西北和甘肃。
长征的路线大半是产米地区,每天每顿都是米饭。有时想办法换口味,假如寻到猪油、面粉,又能从老百姓家中借得平锅,就自己做锅贴。我们都是南方人,不知吃水饺是件大事,无论如何,一样的材料,一样的做法,经过煎烤,锅贴比水饺香。愈做手艺愈纯熟,我们的锅贴甚至出了名。
过云南宣威时,弄到大批火腿,但是炊事班把它剁成块状,放进大锅,掺上几瓢水煮。结果火腿肉毫无一点味道,剩下一大锅油汤。有的人很精,要求不向公家打菜,分一块生火腿,自己拿去蒸,大家这才知道宣威火腿应该怎么做。在这点上,其中肖劲光的收获最大,他的菜格子除留一格装饭之外,其他几格全装了宣威火腿。
长征路上最苦的一段应当是在川西北的两三个月。那时不开大锅饭,每人分的口粮规定吃五天,实际上我两天半、三天就吃完了。准备大饿两天。可是当行军到一个地方时,有村落,地上有新的豌豆苗,有萝卜干,还找到酥油,即牛奶油,我分得一大茶杯。吃了黄油,不但精神抖擞,而且它的营养价值极大。那时,董必武同我们一路行军,有个人还送他半只野羊腿,他就交给我们做,讲明平均各分一份。
进入甘肃后,有一晚在甘肃临洮县属的哈达铺,几个人合资用一枚银元买了一只羊,请卖主杀掉,羊皮归卖主,羊分为若干种做法,当然有羊肉锅贴。只用了一顿,我们几个人当晚就把一只整羊吃了。
根据以上李一氓的回忆,中共宣传与历史记载存在明显差异。中共强调“红军吃草根、树皮,还煮皮带吃”而参与者的回忆却显示在大部分地区和时间里,红军能够享用大白米饭,甚至在某些地区能够获得较为丰盛的餐食。李一氓等人能够制作锅贴、烹饪野羊腿、处理宣威火腿等,表明红军中也不缺有烹饪技能的人。
二、遵义会议期间的生活:被刻意删除红军伙食较好的记载

红军干部到了遵义就上街下饭馆。(图片来源: 网络图片)
港媒《东方日报》曾报导,大陆历史学者高华发现,官方有意删除了一些描述红军生活条件较好的记录:
1954年中宣部将《红军长征记》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在内部发行,但删除了描写红军吃喝玩乐的部分文章。被删除的文章包括何涤宙的《遵义日记》等五篇。
在这些被删除的文章中,何涤宙详细记录了红军在遵义期间的饮食和生活情况:干部团(红军大学)的几个红军干部在1935年初进入遵义城后的十天里,经常去饭店点菜吃饭,吃炒辣鸡。还利用空闲时间,把打土豪获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缝店改做皮衣。
而历史学者刘统在整理《红军长征记》时发现,何涤宙的《遵义十日》内容尤为生动:红军到了遵义,干部团放假了,大家可以上街。上街之后,大家去下饭馆,走那么远的路也没吃着什么好东西。饭馆做的辣子鸡丁特别好吃。于是回去以后,就跟同事们说,那家饭馆辣子鸡丁特别好吃,明儿咱们再去吃。
这些红军干部不仅在遵义享用餐馆美食,还与当地学生联欢,当然少不了吃喝玩乐:“文中还讲到,红军干部跟遵义的学生联欢,遵义师范学校的学生来跟红军干部团联欢。先打篮球,结果红军这些干部,打篮球那些人都是留过洋的,不是留法的就是留苏的,他们这些人平时在瑞金的时候就一块玩球,结果这会在篮球场上,喊的那些口号,防守、上篮,都是用的英文术语,把遵义这帮学生给镇住了。”
这些被隐藏的历史片段,为什么会被刻意从官方叙述中删除?历史学者高华认为:“这种认知和印象,是中共按照其政治需要而不断进行删改、编造的结果。”
三、“红军长征”的真相:假抗日、真逃亡
著名历史学家辛灏年先生则更进一步指出:“蒋介石领导的14年抗战是血写的事实,而共产党所宣称的自己是抗战的‘中流砥柱’是谎言,中共的所谓的‘长征”实际上是假抗日、真逃亡。”
辛灏年认为,长征并非官方宣传的“北上抗日”,而是在国民政府第五次“围剿”下的被迫撤退。1934年秋天,大肆进行共产苏维埃红色武装暴乱的中共红军,被国民政府第五次围剿打得惨败,不得不开始仓惶逃亡,中共将其美化称为“长征”。中共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节节败退,江西中央苏区几乎全部丧失,为了避免全军覆没,才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这与官方宣传中“北上抗日”的说法截然不同。
辛灏年先生通过大量史料考证,当时中共开始长征时,并未提出“北上抗日”的口号。直到1935年初,中共在遵义会议后,为了摆脱“叛徒”、“逃跑主义”的形象,才逐渐提出并强化了“北上抗日”的说法。这是一个事后构建的政治口号而已。
他特别指出,从长征路线的选择来看,如果真正目的是抗日,完全可以选择更直接的路线北上。但实际上,红军长征经过了曲折迂回的路线,反映出其主要目的是摆脱国民党军队的追剿和寻找新的根据地。
辛灏年引用了多位中共高级将领的回忆和文献记录,以证明长征并非为抗日而进行。例如,周恩来在1935年2月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承认:“长征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被迫进行的战略转移,目的是保存革命力量。”毛泽东在长征初期的讲话和文件也显示,当时并无明确的“北上抗日”计划,而是强调“保存实力”和“寻找新的根据地”。
遵义会议争论的核心是军事路线问题和党内领导权问题,而非抗日战略。在四川与张国焘分裂时,争论的焦点是去陕北还是去四川建立根据地,同样与抗日无直接关联。
可见,中共领导层在长征中的主要考量是党的存续和发展,而非抗日民族大义。
红军到达陕北后,并未立即展开抗日行动,而是集中精力恢复和发展实力,巩固根据地。直到西安事变后,国共再次合作抗日,中共才真正参与到全国性的抗日战争中。
1936年红军到达陕北后,外遭国军围剿,内部财物极为短缺,陕北地瘠民贫,很难养活几万人的军队和干部,到1936年冬天,中央党部和红军实际上已经陷入极端困境。正是这种困境,促使中共领导层寻求与国民党的合作,而抗日成为了有利的政治筹码。
辛灏年认为,在中共的抗战叙述中,他们宣称自己是“抗日的中流砥柱”,而长征是“北上抗日的伟大壮举”。然而,真实的历史是,国民党军队承担了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进行了22次大型会战,伤亡320万人,而八路军、新四军在相同时期的伤亡不足20万。中共在抗战期间的主要策略是'发展壮大自己,在战略相持阶段积蓄力量,为的是在抗战胜利后与国民党争夺政权。将长征美化为“北上抗日”是中共建政后为合法化其政权而创造的历史叙事,是典型的历史重构。
其实,不少国际学者的研究也支持长征实为战略撤退的观点。西方历史学者本杰明.杨在《毛泽东传》中明确指出,长征最初的决定是为了逃避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其后才逐步赋予了“北上抗日”的政治意义。历史学家威尔逊在《一九三五年长征:中国共产主义生存斗争的史诗》一书中同样指出,长征的最初目的是生存,而非抗日。
来源:看中国
短网址: 版权所有,任何形式转载需本站授权许可。严禁建立镜像网站.
【诚征荣誉会员】溪流能够汇成大海,小善可以成就大爱。我们向全球华人诚意征集万名荣誉会员:每位荣誉会员每年只需支付一份订阅费用,成为《看中国》网站的荣誉会员,就可以助力我们突破审查与封锁,向至少10000位中国大陆同胞奉上独立真实的关键资讯,在危难时刻向他们发出预警,救他们于大瘟疫与其它社会危难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