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佛大學 (圖片來源: JOSEPH PREZIOSO/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5年7月3日訊】5月29日中國女留學生蔣雨融在哈佛大學畢業典禮上的演講,在美國並沒有引起什麼迴響——後來美國媒體的大事報導也多是評論此事在中國國內造成的輿論海嘯。雖說是「歷史上第一個中國女性在哈佛大學畢業典禮上致辭」,但美國人見多識廣,連異裝變性閹割陰陽顛倒都司空見慣,這麼點記錄破的又算個屁呀?而且哈佛大學作為「左派瘋子」的大本營,其五花八門、匪夷所思、刷新底線的創舉、創新、創造一向層出不窮,大家早已見怪不怪,更漫說什麼「英語不標準」——這才顯示出種族和文化多元呢——、人和衣服不漂亮——美國人審美標準本身就稀奇古怪,尤其在對象是東方的人和物時——、內容假大空——這些敘事人們習以為常,耳朵都聽出了繭子——、表情聲音動作誇張表演——好些美國人的煽情尺度可比這大得多了——這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了。再加上美國人的善良、寬容、厚道、教養、客氣,即便是右超級派和極端厭華者,除了聯想一下習近平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和中共自己吹噓的「哈佛是第一海外黨校」外,都絲毫沒有、也絕不會對一個22歲的異國女性個人刻意的評論、指責、懷疑和辨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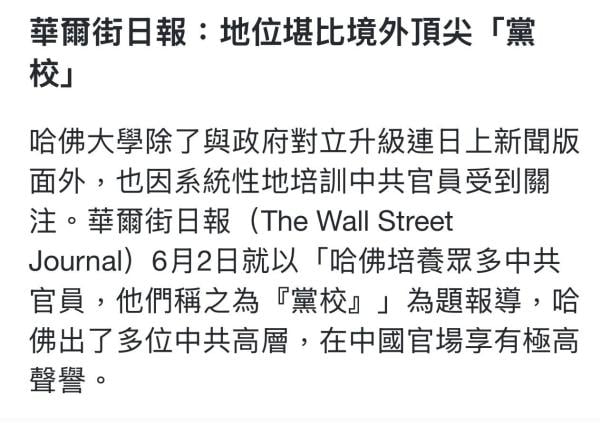
至於美國中文媒體紛紛渲染的所謂「蔣雨融這套‘常春籐精英話術’讓美國普通草根、民粹如何如何不滿和反感」,則完全是瞎扯:淳樸、簡單、現實的美國紅脖子們要關心、參與的家事國事多了去了,他們才不會對一個大學——哪怕是世界第一名校哈佛——與一個大學裡發生的事情投入什麼興趣和關注呢,尤其是還涉及到了他們根本不瞭解也不想瞭解的遠在天邊的中國。
然而,讓美國人無論左傾右向都始料未及的是,蔣雨融及其演講內銷回她祖國後,和原產地的善良、寬容、厚道、淳樸、簡單、現實、教養、客氣每一樣都截然相反的邪惡、狹隘、刻薄、歹毒、卑劣、陰險、腹黑、粗俗的洗產地羅剎國裡,卻無中生有的對這樣一個小人物的一樁小事件掀起了鋪天蓋地的口誅筆伐。
中國極權政府對政治和社會的殘暴統治、對思想和言論的嚴酷控制,使羅剎國人民能參與的事務、能談論的議題極為有限,於是他們尚未被徹底根治、滅絕和鏟除的殘存慾望,就像龔自珍寫的病梅一樣,「斫直,刪密,鋤正……斫其正,養其旁條,刪其密,夭其稚枝,鋤其直,遏其生氣」。其中,蝗蟲般的微信公眾號是這種歪長橫斜最惡劣和最噁心的代表:他們放著權貴高官不敢罵也不能罵、放著黨國大事不敢評也不能評,只好把全部精力、才能和裝逼都放在了緊盯著無權無勇者的芝麻大社會新聞上,稍有風吹草動,就像蒼蠅見了腥一樣一擁而上,死纏無聊事、欺負老實人。哪件事和哪個人一旦不幸讓這群無良無恥無行的蠅蛆們蹤上,都將被啃嚼的瞬間屍骨無存,國內「哈佛中國女生演講輿論事件」,只不過是最新的一個例子罷了。
蔣雨融自己看到的網路上「污穢不堪的下三路訊息和辱罵」不必一提,把涉嫌進行「人類命運共同體」大外宣的蔣雨融栽贓成配合西方勢力的工具和「美國代理人」、把美國確信「和中國政府關係密切」的綠髮會反誣成「美國資助來進行和平演變、顏色革命的非政府組織」的人渣和學渣瀋逸的誅心之流也不值啟齒,只說一下可以用下面這篇文字代表和概括的最普遍、最集中的圍攻和網暴內容: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蔣雨融的演講卻在中國國內遭遇了群嘲和質疑,似乎連哈佛的顯赫地位也不那麼香了。……
在極短的時間裏,蔣雨融的背景就已經被扒了出來,她的父親是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簡稱中國綠髮會、綠會)的執行主任,而她是綠髮會的長期志願者,也曾經得到該會秘書長周晉峰給哈佛的推薦信。……
然而,這不正說明瞭精英與公眾之間的對峙,已經臻於慘烈。人肉者幾乎本能地相信,這些高調的精英背後,一定有著不可告人的暗箱操作……
其實,澄清和辯護,已經足夠說明部分公眾對於蔣雨融的質疑,甚或反感。
蔣雨融的長文,都在竭力說明,自己未曾仰仗父親的地位、金錢或者特權來獲得哈佛的成就,一切都是在母親的含辛茹苦與自我的努力中獲得。但是她卻無法說明,或者故意忽略在綠髮會中所獲得的便利。
公眾簡單地選擇了不相信,反而更加相信她的成功,恰恰是因為起點的不同。她從青島出發,歷經了英國與美國數個頂尖的中學與大學,如此流暢與順遂,的確無法讓人簡單採信她的一切與家庭背景無關。……
但這不是公眾關心的焦點。當成千上萬中國大學生畢業即失業,當無數學子折戟考公戰場,當數以萬計的寒門子弟被擋在985、211的門外時,人們會本能地相信,這個也許在公權部門中不值一提的非政府組織,一定在她的成功中扮演了非同尋常的作用。……
10年來,或者5年來,什麼東西發生了改變?因為以前我們曾經相信儘管結果可能並不公平,但起始是公平的。而今大眾傾向於相信,恰恰是起始的不公平導致了結果的不公平。……
我們或許能夠相信你的成功出自於你的努力,但是我們卻連努力的機會都沒有。這才是網上那些人質疑蔣雨融的本質。
她在回應中引用了孟子的話「雖千萬人吾往矣」……我不知道她未來會不會發覺自己誤用了這句充滿對抗的名言:挑戰她的人並不是挑戰她相信的道理,而是認為,自己是被她的成功所侮辱和損害的人。
她根本不知道自己錯在了哪裡。這就是這一代精英的傲慢與對世界現實的冷漠。……
我認真地研讀了蔣雨融的演講。表演痕跡很重,每個動作經過精心設計;內容並不走心,而是刻意引發現場效應;主旨老生常談,毫無任何創新與創意,只不過在重複老套的全球主義話題。
哈佛選擇了蔣雨融,實際上是明確地選擇全球化。……
蔣雨融的演講內容,或者在哈佛的原則堅持,都沒有錯。甚至可以說,哈佛更加道德高尚,理想遠大。
哈佛所看不到的是:人們真實地並不是在反對全球化,而是反對全球化的結果。是在近半個世紀的全球化中,精英們收割了全球化的所有果實與榮譽。
蔣雨融代表的並不僅僅是她自己而已,而是哈佛這個精英機構的意識形態。當她和哈佛還在侈談全球中的眾生平等,動植物權益和綠色進步的時候,普通的公眾卻始終焦慮於通貨膨脹、工作機會和日常安全。
在這場針對蔣雨融和哈佛的冷嘲熱諷中,中國與美國的公眾突然一起「環球同此涼熱」了。公眾看見了民粹主義:對於個人信息與權利的肆意入侵,與對大學獨立精神的侵犯。但公眾所無法看見的是:自己正在不斷強化與催化民粹主義的甚囂塵上。
哈佛不回應在全球化中受損的人的困境:那些都是太過於人間的問題。這就是精英機構的傲慢與冷漠。……
他們並不理解,也不想理解在中國與在美國的普通公眾的現實痛楚與困惑,不想向他們解釋這一切不公平發生的緣由……
蔣雨融與哈佛都不知道自己錯在了哪裡,因為他們始終仍然在堅持精英的傲慢與冷漠。如果這一代的精英和精英機構,依然無法理解民眾的困頓,與世界的改變,那麼,公眾的反叛,將會再次製造洪水滔天。
在國內欺軟怕硬、宵小勢利的所有唇槍舌劍、嘴炮口彈中,都不約而同地對「精英」進行了控訴、討伐和攻擊,而這也是近幾年中國輿論場上的一個「目睹之怪現象「——如果非要說中國還有輿論的話。
「精英」一詞,在今天後浪廢青以及蔡奇這類低端人口的耳朵裡固然很陌生,但我們這一代人太熟悉了。上世紀八十年代直至「六四」前夕,「精英」(Elite)至少在知識界和大學裡是一個人口皆碑的流行詞。那年頭「精英」僅僅指知識精英——其他行業即使有佼佼者,也是夠不著「精英」的不入流——,他們是高校學子和一般關注社會者青睞、傾慕、嚮往和勵志的對象。「六四」屠殺後,共產黨將當時公認的所有知識精英一網打盡、斬盡殺絕,「精英」一詞也隨之絕跡。多少年之後,「精英」重出中國江湖,竟然成了文化人嘴裡抨擊、責難、中傷、貶低的對象,被陰陽怪氣得一無是處。但是,精英的意義和作用不光不可抹殺,而且舉足輕重:引領人類、開闢時代、奠定未來的從來都是一批又一批的精英們。歷史當然是極少數英雄創造的,而絕大多數人則只是群氓和群羊。當代中國人之所以否定、拒絕、摒棄和仇視「精英」的根源,一是共產黨長期「虐民、弱民、貧民、疲民、辱民、愚民」的統治和壓迫造成了全民族擺爛、犬儒、自輕自賤、破罐破摔和「我是流氓我怕誰」;二是共產黨多年黑白混淆、是非顛倒、人妖不分的精神污染,早已讓當代中國人根本搞不清什麼是「精英」,他們理所當然的認為有權有勢、財大氣粗、有名有利有流量的「投胎能手」、「國民老公」、「人生贏家」等就是「精英」,繼而在羨慕嫉妒恨的依次心理下去對一切「精英」否定、拒絕、摒棄和仇視;三是共產黨的心理和自己奴隸、奴才們以為的正好相反,它從始至終自卑到骨頭裡,從不敢把自己想做精英,而是蓄意把自己的罪衍和作孽全部栽贓、轉移、嫁禍到精英們的身上,並用慣用的仇恨教育伎倆煽動老百姓的憤怒和怨毒。上面文字裡那些製造、挑動、渲染和激化「精英與公眾之間的對峙,已經臻於慘烈」、「這些高調的精英背後,一定有著不可告人的暗箱操作」的作者,不是中了共產黨的陰謀圈套,就是刻意助紂為虐、幫助共產黨「挑動群眾鬥群眾」。
任何一個社會都會有不同的階級和階層,「消滅階級和三大差別」、「等貴賤、均貧富」是早期共產黨人畫的大餅和野心家們的欺世盜名。蔣雨融和她爸爸算得上算不上精英不去評論,即使是精英而且培養、製造出了下一代精英也再正常不過。蔣雨融「她的父親是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簡稱中國綠髮會、綠會)的執行主任」沒有任何過錯,她因為父親爸爸的原因「是綠髮會的長期志願者」並且有助於進入極其重視社會服務實踐(Community Service)的美國大學哈佛學習沒有任何不當,她「曾經得到該會秘書長周晉峰給哈佛的推薦信」更是自然而然——如果周晉峰拒絕給她寫推薦信反倒說明不是他的情商智商就是她的行為品性有著大毛病。連自由平等寫入骨髓、血液和基因的美國裡,常春籐這樣的私校都講究關係、人脈和家庭背景,都為校友的親屬提供機會和方便。「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這是自古以來的自然現象和人生經驗,用陳伯達的話叫「理當如此」。精英不是趨炎附勢、俗不可耐的當代中國人眼裡權勢、地位、財富的代名詞;精英不可以世襲、但大概率可能傳承,只要不是世襲就無可厚非。北大既沾不上官也沾不上富的校友們給自己孩子發明瞭一個詞叫「學二代」,如果北大「學二代」們外上不了哈佛、內不見於北大,那才真的是父母或孩子出了讓人笑話和抬不起頭的大問題。
與此同時,在北大看慣了不計其數赤貧的農家子弟成為了高官、巨富、學閥、名流和更加數不勝數的高官、巨富、學閥、名流子孫淪為碌碌余子的我,從來不相信起點不平等決定了人的一生,也始終確信「階級流動停滯」、「上升通道消失」、「命運無法改變」等等陳詞濫調,既是三和大神擺爛、躺平的藉口和擋箭牌,更是共產黨統治集團、權貴階級、門閥氏族蓄意讓奴隸們心甘情願的自承屌絲、螻蟻、草芥、韭菜的陰謀話術。
「能接受結果的不平等而必須要求起點平等」的是美國人,中國人奴隸當慣了,其實根本就不在意起點是否平等,「羨別人的爹,恨自己的命」是中國人的常態。非要相比的話,中國人倒是對結果的不平等更在乎、更憤恨、更不平——中國人是最喜聞樂見和心滿意足的,就是一個「投胎能手」最後成了敗家子和紈絝子弟。四十年前我在北大二教第一次聽老學長胡平的演講,他說到:地位和財富的人人平等並非美善和道德,反而恰是進步的阻礙;只要起點平等,結果如何都屬於公平。他的話在那個年代如醍醐灌頂,如今中國人起點前移,一直到了投胎娘肚子,從此也就再沒有了「起點的平等」——但你並不能說這就意味著世上不存在公平:老天的事誰又能評價得了呢?
不過,結果不平等、不公平也好,起點不平等、不公平也罷,都既和蔣雨融沒有關係,也沒有在她身上體現:以此作為責備她的一個理由,是打錯了板子、怪錯了對象。
不錯,當今「成千上萬中國大學生畢業即失業」,但這是習近平倒行逆施的閉關鎖國、與全世界為敵和三年「清零防空」最終把經濟徹底折騰垮了的惡果;不錯,眼下「無數學子折戟考公戰場,數以萬計的寒門子弟被擋在985、211的門外」,但這是共產黨對權力壟斷獨霸的信念和制度一手造成的,和蔣雨融、蔣雨融的爸爸甚至中央委員會一小撮之外的人沒有一毛錢關係。蔣雨融沒有上北大清華、沒有進央企國行、沒有當官員公幹,已經和今後都不會在國內工作,即便她不適當的佔有了稀缺的資源、擠掉了別人的機會,她擠佔的也是美國的稀缺資源,而沒有妨害其他中國人的機會、沒有損害任何中國人的利益,大多數中國人「連努力的機會都沒有」無論如何也怪不到她的身上。這些指鹿為馬的幫凶、幫閑們不去追究那些真正予取予奪的人群的責任、不去譴責那個窮凶極惡的政黨的罪行、不去清算那個禍滿人間的制度的孽債,卻拿八竿子打不著的蔣雨融出氣,將他人的罪過強加到莫名其妙的蔣雨融頭上,把責任一股腦兒的讓無辜者承擔,讓憑空而來的陰影籠罩她一生,她招誰惹誰了?
至於指責蔣雨融無視維族人被囚禁、維權者被打壓、異議者被迫害、法輪功被活摘、超生人被追捕,不去揭露鐵鏈女和底層民眾水深火熱、食不果腹、衣不遮體、無法生存,則純粹是欲加之罪:她是對哈佛講話,她的父母工作生活在牆內,你讓她當著全世界的面大聲疾呼、控訴共產黨侵犯人權和生存權,這不是神經病嗎?再說,一個自小生活在大城市、受著共產黨傳統教育、對政治陌生遠離的中產階級女孩,可能對這一切真的是一無所知。指責她的視而不見、精英而空洞,不如去譴責習近平的愚弄欺騙、既敗類又沒有人話。
蔣雨融哈佛畢業典禮上演講的初衷、內容、理念和主旨與中國都毫不相干,但結果到了國內卻讓她「她彷彿陷入了一場雙面夾擊——既是‘西式精英話術’的操弄者,又是為‘體制背書’的既得利益者,兩種意識形態標籤彼此矛盾,卻共同指向她本人」。當前中國社會蘊藏著巨大、尖銳和激烈矛盾,洋溢著衝天戾氣、怨憤和不滿,共產黨有意禍水東引、嫁禍他人,誘使羊群們先是把富人當成出氣筒、繼而把憤怒發泄在任何出名冒尖者、鶴立雞群者、不同凡響者、木秀於林者、獨樹一幟者身上。那些被「侮辱和損害的人」只有認識到:「侮辱和損害」自己的另有罪魁禍首,和蔣雨融及其成功沒有任何關係,必須把自發、情緒、歧途的反精英和反特權轉化和升華為自覺、理性、正確的反抗共產黨及其暴政,這樣才能擺脫被「侮辱和損害」的狀態,改變命運、獲得未來。至於蔣雨融「不知道自己錯在了哪裡」,是因為她根本沒有任何錯,也不需要承擔不屬於她的負疚。
至於說什麼「在這場針對蔣雨融和哈佛的冷嘲熱諷中,中國與美國的公眾突然一起‘環球同此涼熱’了」、「哈佛大學也不想理解在中國與在美國的普通公眾的現實痛楚與困惑」、「如果這一代的精英和精英機構依然無法理解民眾的困頓與世界的改變,那麼,公眾的反叛,將會再次製造洪水滔天」,則是赤裸裸的為共產黨解套、為共產黨貼金、為共產黨洗白、為共產黨背書,將共產黨邪惡制度造成的災難曲解為中美乃至全球共同的處境,用心險惡、卑鄙又拙劣。美國固然有美國的問題,美國普通公眾自然有美國普通公眾的現實痛楚與困惑,美國人民當然有美國人民的不滿和抗爭,但與中國的災殃和禍殃神鬼殊途、人妖兩界,與中國普通公眾的不幸和苦難天上地下、雲間泥裡,與中國人民的怒火和義憤星火烈焰、響鼓驚雷。美國公眾的反叛,會不斷使美國鳳凰涅盤、慾火重生、蛻變更新;而中國人民的忍無可忍,將掀起狂飆巨浪、造成火山噴發,使共產江山洪水滔天、土崩瓦解、徹底覆滅。
「世上若有女性買不起衛生巾,便也是我的貧困;若有女孩因懼怕騷擾而輟學,便是我的尊嚴受辱;若有孩童死於他既未挑起也不理解的戰火,便是我生命的一部分隨之而亡」,不管是出於至誠還是煽情,但蔣雨融的的確確發出了這一聲音、口口聲聲說出了這些詞彙,羅剎國中人要心理變態到什麼程度才會聽出「這就是這一代精英的傲慢與對世界現實的冷漠」?單純誠信、與人為善、「你說固你是」的美國人,恐怕永遠也想不出答案。
真理都是老套和老舊的,普世價值更是老生常談,當然這些還都比不上基督教教義幾乎「毫無任何創新與創意」但卻歷經千年、長盛不衰。
哈佛大學作為世界第一學府和精英勝地,其堅守和訴求的就是道德、高尚、理想、真理。不但如此,連「真理(Veritas)」做為哈佛大學的校訓也還是後來的事呢:哈佛校訓1650年是「榮耀歸於基督」(In Christ),1692年是「為基督為教會」(Christo et Ecclesiae)。哈佛早期印章上是三本翻開的書,兩本朝上、一本朝下,寓意著理性(reason)與啟示(revelation)的關係;哈佛最早期文獻、1642年的《學院法例》寫道:「讓每一位學生都認真考慮以認識神並耶穌基督為永生之源,作為他人生與學習的主要目標,因而以基督作為一切正統知識和學習的惟一基礎。所有人既看見主賜下智慧,便當在隱密處認真藉著禱告尋求他的智慧」。可見,哈佛從一開始的立意就是獨立於世俗——更別說獨立於黨派、政府、群體和集團了——而直接面向上帝的終極之靈,從一開始的信念就是真理和智慧掌握在上帝手中,人類要做的只是一步步接近和認識它們。哈佛這類精英私立大學不是黨校,不是智庫,不是政策研究室,不是「五道口職業技術學院」和山東藍翔;它們生來就是要「不問蒼生問鬼神」,生來就是為了「侈談全球化中的眾生平等,動植物權益和綠色進步」之類的命題。至於「在近半個世紀的全球化中,精英們收割了所有的果實與榮譽」、「普通公眾的現實痛楚與困惑」、「普通的公眾始終焦慮於通貨膨脹、工作機會和日常安全」、「民眾的困頓與世界的改變」等等等等,都不是它要考慮的問題和承擔的義務。哈佛「不回應在全球化中受損的人的困境」、不關注「那些太過於人間的問題」、「不向人們解釋一切不公平發生的緣由」,不是「這一代精英機構的傲慢與冷漠」,而是它自始以來堅守的價值和原則。
哈佛的「道德高尚、理想遠大」不是問題,哈佛的不問人間、不務世事、不謀稻粱不是失誤,哈佛的關注宏大和抽象也不是過錯——基督教關注的更宏大和抽象呢——;它的問題、失誤和過錯恰恰在於如今忘記了自己的初心和使命,放棄和偏離了中立、客觀、實用的本分,開始熱衷世俗、干預世事,站隊了意識形態、選擇了方向立場、介入了黨派對立、參與了路線之爭,企圖為社會尋找出路、謀圖為世界設計前途、妄圖為人類指明方向;而書生們一旦要這樣做,必然走上歧途、偏離正道、壞了大事,五四時代的知識份子就是慘痛的前車之鑒。更有甚之的是,哈佛完全不記得二十世紀人類以億計生命為代價換來的教訓,再次確信只有自己發現和掌握了宇宙真理、創造和找到了美麗新世界藍圖及其實現路徑,重新認定自己可以並且應該消滅掉那些阻礙歷史前進和人類幸福的異端與邪說、精神和思想。
對一個「只是談了一些關於‘共同人性’的普世價值」的演講,羅剎國中人或者像人渣和學渣瀋逸那樣將其歪曲成「配合西方勢力」、「做美國代理人」,或者攻擊和譏諷它「操弄西式精英話術」,或者拾人牙穢的去用另一個華人學生Andrew Yang的同期哥倫比亞大學工學院畢業演講去貶低、醜化蔣雨融的「假大空」。他們在振振有詞之下,卻露出了西裝裡面的山西花褲衩——「只許洋婆子出軌,不准隔壁家偷人」的中國自卑與嫉妒心態:洋人無論講人類、世界、全球還是太空、外層空間甚至天堂來世都尋常和自然,距離洋人幾個次元的自己家土豹子跟著鸚鵡學舌就是無法忍受的刺耳彆扭和不可饒恕的裝逼賣萌。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他們說的倒也恰如其分:蔣雨融口吐的蓮花和中國現實離得太遠了,成年人才該幹的事,你小屁孩跟著攙和、搗亂個什麼呀?好萊塢電影裡美國人拯救了世界、地球、人類之和平、環境、生存的題材比比皆是、司空見慣,中國電影要是同樣拍,國人自己都會罵成爛片;中國人看通貝裡的行為也沒覺反常和驚訝,因為洋人世界無奇不有、見怪不怪,中國小孩要是同樣幹,不用國保公安出面,她爹媽就會一腳把她踢回家:快去寫作業!
面對祖國羅剎蔣雨融沒有錯,不需要承擔不屬於她的負疚;面對美國蔣雨融也沒有錯,不該受到指責:追求榮譽和輝煌、渴望眾目睽睽的注視和眾人仰望的舞臺、驕傲自己贏得的成就和掌聲,這些都是人之常情,除非是在共產黨蹂躪、踐踏下習慣了擺爛躺平的中國當代青年;內容宏大空泛、執守精英情懷、脫節尋常百姓,可是既然在哈佛演講,不講這個常春籐標誌性的話語講什麼?講「美國第一」、講「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講川普(特朗普)對哈佛的控訴如何正確嗎?
難道年僅22歲、在美英進步主義大環境和哈佛精英激進小氣候裡熏染了好幾年的她不會是出自真心和真誠嗎?難道面對幾千名呼吸與共、彼此烘托、互相激發的同溫層,她不可能真的悲傷、真的憤怒、真的感動嗎?陶傑相信「那一刻讓我想起了我小時候曾經相信的事情,即世界正在變成一個小村莊。我記得有人告訴我,我們將是第一代結束人類飢餓和貧困的人」是蔣雨融的蓄意編造,因為她「小時候曾經相信的事情」一定是「做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一定讓共產主義在我們這一代實現」;話雖不錯,但目睹了這麼多年畜生餓鬼、鬼蜮惡道,又沐浴過歐風美雨、人間正道的她,就不可能早已把連共產黨核心和領導集體們都丟在垃圾堆裡的信仰和誓言忘的干乾淨淨了嗎?即便是編造,要作文也只能如此才符合內容的邏輯;而且寫文章的人都知道,編著編著自己就會信以為真,越來越覺得那就是真實的存在。
如果說到錯、說到該譴責,錯的是哈佛大學、該譴責的更是哈佛大學。左派大本營「哈佛的哲學就是鬥爭哲學」:川普發出哈佛國際學生「禁召令」,川普政府特別強調和專注對抗、打擊中國,盧比奧嚴加審查並威脅撤銷中國留學生簽證、保守派弘揚天理人倫、重男輕女和討厭DEI,哈佛偏要和川普針鋒相對、以牙還牙,偏要反其道而行之、給川普迎頭痛擊,偏要選一個中國的女國際生作為哈佛標籤來弘揚自己的意旨,偏要讓一個中國人來為美國和世界詮釋什麼是自由、寬容、多元、DEI。當然這一切在民主、自由、法治和政治對立公開合法存在的美國也都不算錯,哈佛錯就錯在讓一個不但來自、而且在外人眼裡也代表著有史以來最反動、最專制、最保守、最封閉、最邪惡、最殘忍、最暴虐、最反文明、最毫無人性、最政治不正確、最抗拒和違背普世價值政權的留學生來充當佈道者,站在全球第一學府、自由意志堡壘的講台上,教育全美國、號召全世界、指導全人類要如何「守護共同的人性」、「尊重不同的意見」、「接受彼此的差異」、「保持同理心和善意」,從而把自己一貫自詡獨霸的道德高地拱手讓給了那個有史以來最反動、最專制、最保守、最封閉、最邪惡、最殘忍、最暴虐、最反文明、最毫無人性、最政治不正確、最抗拒和違背普世價值的政權。哈佛錯就錯在它口口聲聲講意見多元、言論自由、表達寬容,卻在中國大使謝峰來校講演期間毫不猶疑地把在場抗議的臺灣學生拖出門外。哈佛錯就錯在它不但認為中國最親、最具力量、最值得重視,而且相信中國最適合、最有資格傳播自由、平等、多元、DEI。哈佛錯上加錯的是,你那麼悲天憫人、那麼情系天下、那麼大愛無疆、那麼「老吾及人幼吾及人」,卻不僅對滿目皆是、遍及華夏的在禁錮、迫害、凌辱、壓榨、折磨、驅趕、刑求下呻吟哭號、掙扎煎熬的男女老少們不發一聲,而且恰如白宮指控的那樣和這個政權眉來眼去、暗通款曲、勾連共謀。即便左派把持的哈佛對社會主義無限的心嚮往之,但它至少該明白: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根本就不是他們理想和追求的那個「美麗新世界」,它至少也該懂得:左派理應也實際上比右派更關注、熱衷普世價值和意識形態的維護與推廣,像左派的前輩卡特一上臺即以「人權」為外交的指南,像左派的另一個前輩拜登雖然和中共千絲萬縷但仍然不得不出手狠辣。哈佛左了一輩子、進步了一輩子,在中國事務上卻徒有其名,連最基本的立場和特徵都喪失、丟棄了。在川普咄咄攻勢面前,哈佛已經拿不出什麼像樣的武器抵禦,只好飲鴆止渴、飢不擇食的求助蔣雨融來草船借箭——難怪川普打心眼兒裡看不上它,把它貶低的一無是處、一文不值,真是活該它自作自受呀。
錯的、該譴責的更是侵泡在醬缸裡、卻「子非魚焉知魚之樂」的所有羅剎國中人。
蔣雨融「在演講中只談了一些關於‘共同人性’的普世價值」就被鋪天蓋地指責為「美方代理人」、「西式精英話術的操弄者」,說明中國是多麼害怕和痛恨普世價值、多麼與普世價值不共戴天;蔣雨融在羅剎國的輿論遭遇,證明了它是何等醜陋、落後和愚昧,距離現代文明何等遙遠;而大大小小幫凶、幫閑們的攻擊以及政權的縱容和放任,則說明共產黨對她所講述的內容是如何的反感、不悅和目為指桑罵槐。在美國,哪怕再孤立主義、再美國第一,有著救世精神、宗教情懷、山巔意識、燈塔信念的美國人也不會否定蔣雨融弘揚的那些基本的普世價值。普世價值絕非左派的專屬和精英的傲慢,保守派也不可能把自由世界的旗幟撒手丟給左派。保守派反對左派不是反對普世價值和精英傲慢,而是痛恨左派天天把普世價值掛在嘴邊欺世盜名、拉大旗作虎皮,搞腐敗、販賣私貨、兜售社會主義、與中國私相授受和實質上徹底背叛普世價值。
5月29日,22歲的蔣雨融走到了她迄今為止人生的最高光時刻。在全場的掌聲雷動和會心笑聲中,她一定會更加堅定的確信自己信奉和宣揚的理念是人類共同的信念、追求與價值。然而,僅僅幾天之後,現實就給了她重重一擊:這個世界上根本就沒有「共同的人性」——至少在她學成的哈佛和她長成的中國之間沒有。而告訴她這個殘酷事實的,不是哈佛仇恨的美國而是她母校熱愛的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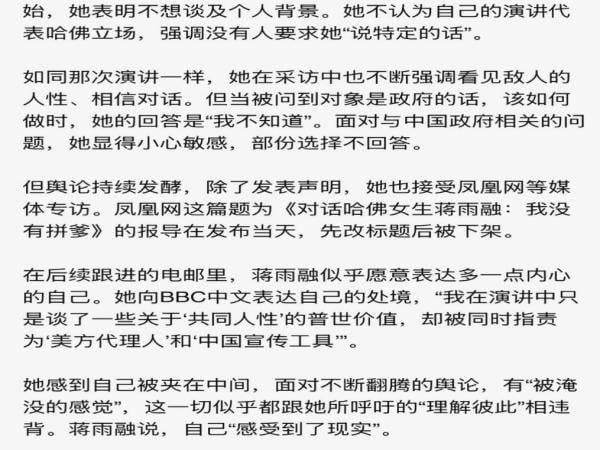
在回答BBC採訪時,蔣雨融早已經沒有了幾天前的揚眉吐氣和豪情萬丈,明顯的灰心喪氣和無所適從:「我在演講中,只是談了一些關於‘共同人性’的普世價值,卻被同時指責為‘美方代理人’和‘中國宣傳工具’。她感到自己被夾在中間,有‘被淹沒的感覺’,這一切似乎都跟她所呼籲的‘彼此理解’相違背。蔣雨融說,自己‘感受到了現實’」。不過,蔣雨融仍然沒有意識到另一個更重要的事實:她對政治不懂也沒有興趣,始終只談人性、「強調看見敵人的人性、相信對話」,對美國和中國的政治同時迴避,既害怕承認自己的演講是在向特朗普政府放話,也在「面對與中國政府相關的問題」顯得小心敏感、不予回應,而當被問到「對象是政府的話該如何做」時,她乾脆就一概回答「我不知道」——就在這一刻她露出了中國製造的底色和原形,一點也不哈佛——,但政治卻找上了她、纏上了她。這種結局,固然出於自己的無知,但哈佛的瞞騙也功不可沒:哈佛標榜自由精神、獨立人格、「與真理為友」——VERITAS,實際上有著明確的意識形態、政治傾向並旗幟鮮明的介入了兩黨政治爭端。蔣雨融做了中國宣傳工具是假,但成為哈佛對付川普的模擬槍是真。
但蔣雨融必須成長。她不應該只是無奈和茫然,而應該去想、去想到更多更多。她應該重溫她父輩們如數家珍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基本原理:人類社會中只有階級性,而從來沒有抽象、一般的人性。她不應該只是看到、承認和接受「理想主義和與現實的差距」,還應該「直面慘淡的人生、正視淋漓的鮮血」,打破我們從小就被批判透了的資產階級「人性論」和「愛的囈語」,勇敢的面對政治,致力縮短理想與現實的距離。
當蔣雨融站上哈佛的講臺,作為首個在畢業典禮中致辭的中國女性,面對全世界最聰明、最幸運的一群人的注視,高開雙手,聲情並茂地朗誦她的鴻篇巨製時,她或許也想到了在當前美國攻擊進步主義、排斥全球化、拒絕國際學生、反中抗華喧囂塵上的氛圍下自己有可能遭遇保守者非難並為此做好了思想和精神準備,但她絕對不會預計到,最後給了她毀滅性摧毀的卻是讓她產生強烈炫耀慾望去爭取這份榮譽以及她自以為支撐、自以為底氣、自以為激勵的祖國。如果蔣雨融對她為之驕傲的演講中的信仰、信念是真誠和持久的,經此荒唐鬧劇之一役,她一定會知道從今以後將如何愛和怎樣憎、將如何汲取哈佛的養分和怎樣排棄哈佛的毒素;她一定會知道她腦海和意識裡那個用「割裂、恐懼與衝突去蠶食這個互聯世界的承諾」的勢力、那個「錯誤的認為那些思想相異、投票選擇不同或信仰有別的人都是‘邪惡’」的幫派、那個永遠學不會「與不適共處,認真傾聽」的力量、那個根本不「相信共同的未來」不「相信對話」不承認被自己「貼上敵人標籤的人也是人」的群體、那個不但看不到「他們的人性」更沒有「自己的人性」的黨眾,不是美國的保守派,而是醜陋的令人髮指的羅剎國中人;她一定會知道她大聲痛陳尊重多元、「勿因差異妖魔化他人」的對象不是美國和川普而是羅剎中國與習近平;她一定會知道「守護我們的人性」的前提是必須有人性、是必須結束羅剎中國那種人吃人的制度。從這個角度上說,蔣雨融的遭遇恰好證明她呼籲的不是超前的精英關切,而是對中國正當其時的迫切任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