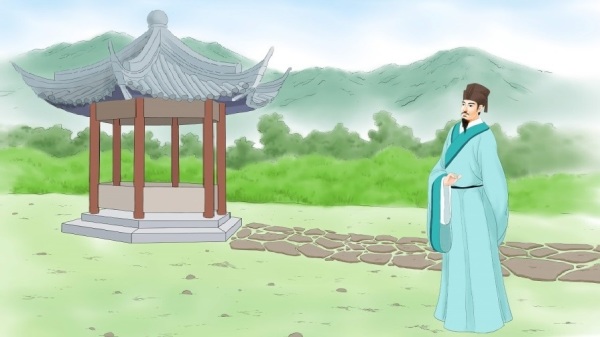
白居易將酒、詩、琴,視作「北窗三友」,而他的詩作有一大半都跟酒有關。(繪圖:志清/看中國)
一般來說,不懂酒者,無詩;不好酒者,無好詩;不善於在酒中覓得詩魂詩魄者,詩人的想像翅膀,也難以高高飛翔起來。白居易將酒、詩、琴,視作「北窗三友」,可是,在他的詩集中,寫琴的詩,其實是屈指可數的,而寫酒的詩,卻比比皆是。他的全部詩歌中,至少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與酒有關。此種現象讓人開始思索,詩人對於酒的這一份眷戀,這一份陶醉,這一份情有獨鍾,是否與《舊唐書》稱:「白居易字樂天,太原人」,《新唐書》稱:「白居易字樂天,其先蓋太原人」的籍貫,有些什麼聯繫?
從古至今,山西是出好酒的省份,所謂「河東桑落酒,三晉多佳醪」,與其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與其豐沛富庶的天然資源,與其傳統風格的釀造技術,與其歷史悠久的地域文化相輔相成。唐代的段成式在《酉陽雜俎》列舉盛唐時期享譽域內的名酒時,河東桑落酒與劍南燒春並列。
白居易飲過的桑落酒,當代人是很難再有此口福了,但近代中國,山西的酒,總是榜上有名。其實我之飲酒,不能滿觴,大有蘇東坡《題子明詩後》一文中所說「吾少年望見酒盞而醉,今亦能三蕉葉矣」的意思。蕉葉,是一種淺底酒杯,容量不大。我就是屬於這類願意喝一點酒,但酒量有限,喝得不多,決非主力的酒友,可是卻很願意在席間,在桌上,在小酒館裡,在只有一把花生米,一個搪瓷缸子,席地而坐,看朋友喝酒,聽朋友聊天。尤其喜歡西漢楊惲所作《報孫會宗書》,嚮往那「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嗚嗚」的激情,期待能夠抒發出自己胸中塊壘的熱烈場面。
1957年,我當了「右派」後,發配去勞動改造的第一站,就在貫穿豫西北和晉東南的鐵路新線工地上。河南這邊,山極高,極陡,極荒涼,山西那邊,地極幹,極旱,極貧瘠。那時,勞累一天以後,鐵路供應站賣的那種散酒,喝上兩口,放頭大睡,曾經是解乏兼之忘掉一切屈辱痛苦的絕妙方劑。起初,瓶裝的山西名酒,還在貨架上放著,頗引得愛酒的我嘴饞。但打成右派,工資銳減,養家糊口,哪敢奢侈,也就只能遠遠看上一眼,聊過酒癮而已。
身在晉地而不飲晉酒,心中總有一點欠缺的感覺。
到了上個世紀的六十年代,物資供應漸顯匱乏之際,別說瓶酒,連散酒也難以為繼了。一次偶然的機會,我也記不得是屬長治市管,還是歸長子縣管的兩地交界處的小鎮上,一家已經沒有什麼貨品可賣,只擺放著牙膏、牙刷的供銷社裡,居然在貨櫃底下,我發現還放著一瓶商標殘損的名酒。我傾囊倒篋,連硬幣都湊上,將這瓶酒拿到手。對著冬日的太陽,那瓊漿玉液的澄澈透明,當時,我的心真是醉了。
將佳釀帶回到工棚,與我那些同吃同住同勞動的工友們共用。冬天,晉東南的丘陵地帶,夜裡乾冷乾冷,寒號鳥叫得人心發怵,帳篷裡儘管生著爐子,也不免寒氣逼人。不過,這瓶酒,卻經過一隻隻手握過來,透出溫馨,透出暖意,尤其後來打開瓶,酒香頃刻間將帳篷塞滿,那時,儘管酒未沾唇,我的這些工友們先就醉成一片了。
有人從炊事班討來一些老醃鹹菜,蔓菁疙瘩,一個個吃得那麼香,喝得那麼那麼美,成為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回味不盡的話題——不過只是一瓶酒,卻能煥發出人們心頭的熱。
他們知道那時的我是右派,也知道我曾經是作家,而且因為寫什麼小說,被打下來的。於是有人問,老李,你不是說過好詩如好酒,好酒如好詩麼?你不來上一首?
我一愣,我還有詩嗎?我靈魂深處還能發掘出來一星半點的詩意嗎?
儘管我馬上想起來白居易的「唯當飲美酒,終日陶陶醉」的詩句,可我卻「陶陶然」不起來,儘管那倒在杯子裡的酒,芬芳撲鼻,馨香無比,其味佳醇,其韻悠遠,但那種政治境況下的我,唯有愁腸百結,只剩滿腹悲愴,竟一句詩也寫不出來。
不過,我倒也並不遺憾,因為在那個年代裡,在那個寒冷的冬夜裡,那瓶使人們心頭熊熊燃起來的好酒,那一張張把我當做朋友的臉,在我的全部記憶中,卻是最最難忘的一首最好的詩。
